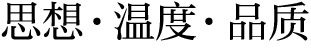2020-07-23 15:07
从2016年4月到今天,两年多过去了,经历了阅读、创作和前期调查采访,密集的工作,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
我所论证的题目是作家和他/她的故乡的关系。这个故乡是实地的故乡,也是他思想的故乡。那么,我就从泛读开始,锁定重要作品之后再精读,最后提炼出要点,形成大纲。前者是保证作家生命体验线索的完整,后者则是探索作家心灵的深度,思想的边界。从作品里寻找人物/原型、故事、叙事方式,结合创作思想的变化,来论证一个作家历经离乡、怀乡,最终通过创作回归一个人的文学故乡,呈现他/她的人生历程。他们是一群从土地和万物汲取营养的作家们,是无数种文学经验当中与土地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群,同时,这也是一种生存经验的转化,这一转化就像种植和收获,就像锻造和提纯,种子从大地汲取营养,吸收阳光雨水,收获粮食,完成酒的酿造。


▌迟子建
张同道老师说我完成了3千万字的阅读量,我没有统计过,但是我通读了能找到的他们的作品,但肯定也有遗漏没有读到的文字,比如莫言的某些创作谈和演讲,贾平凹的散文游记,而一些与此主题有关的重点篇目则是反复阅读,比如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毕飞宇的《玉米》、《平原》。
我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努力最大的是清净自己的心——不让任何既定的文学概念和先前对作家、作品的印象影响我这一次的阅读,这些作家和他的作品在我生命的某个节点上无疑对我产生过莫大的影响,我也会回忆,对照,也会顾及自己的感受,但不去做判断,仅仅是作为一个静静的阅读者,一个静静的倾听者,这样才能离我要了解的人物更近一点儿。《秦腔》里兄弟四人,仁义礼智信,那么大哥“仁”是早早去世了,“信”是根本没有的,失去依怙的乡村众生相。《废都》里的庄之蝶蜕变成了《秦腔》里拔刀自宫的少年引生。这都切中了漫长中国文化的痼疾,也切中了人性的软肋。从道的层面,表皮和内瓤如何在心里融合为一,从世俗层面性情如何会扭曲和丢失,“哀莫大于心死”,这是一个人的体悟和警醒。《生死疲劳》到了最后,就是一句话,“欲望使人深陷轮回,而仇恨是没有意义的。”《檀香刑》则是一个人演化出来的多声部的大合唱,这个合唱从1900年的高密东北乡传过来,这个声音来自《民间音乐》。两位先生更像是艺术家。毕飞宇先生是这个文学链条上的一位,他像是大地上的游侠儿,从河网纵横的《平原》走出来,划着船,从村庄,县城,划到了扬州,上海,南京,因为强烈意识到人的局限,他铆足了劲儿往前冲,他寻找到思想的边界,也找到了文学的故乡,因此也就获得了某种安宁。然而,一切的所为是鼓励观者去阅读原作,那是一个人的独特心灵空间,从中各取所需,提取精华,反诸自身,从中受益。

▌毕飞宇与乡人
工作的方式是滚动式、随机式的,效率高,步伐紧凑,一个接一个,面对面与这些作家们沟通,对不善交际的我也是个挑战。好在他们是最善解人意的一群,特别是莫言先生,对最后形成的文学脚本给了肯定,让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2016年的12月13日,我第一次到莫言先生家里拜访。他在平安里的那间小客厅里接待了我。当我老实说还没有通读完他的所有作品,他开始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某个瞬间,谈话突然间停止下来,整个房间里寂静无声,我忽然意识到天已经全黑了,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暗中,窗外透出的微微亮光映出对面的人影轮廓,而声音却还在回响——写到这里,让我想起来2005年同样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参与莫言先生的北海道之行,但那次我给杂志什么也没有写,我当时是觉得莫言出现在时尚的杂志上是多么不相宜啊,现在我也许不会这么想了,因为时尚也可以重新界定,那次,我整理他在北海道大学的录音演讲时,不也是夜晚寒冷而空荡荡的新居房子里,他一个人的声音在响着吗——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是坐在黑暗中谈话,当然主要是莫言老师在说,而我也完全被他绵密生动的讲述所吸引。这时候,响起脚步声,随即“啪嗒”一声,客厅大亮,是莫言先生的爱人进来开了灯。我忽然明白了,这也是莫言先生写作的一部分。我现在所要完成的不就是这样的呈现吗?也许那些访谈我后来都不能记得许多了,可是这个瞬间却牢牢地印了下来。

▌莫言
对作家故里的拜访让我也深切感到,如果作家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那么他们的根系深深扎在土地上。如高密东北乡的刘连仁,1944年作为劳工被抓到北海道,荒野求生,1958年被当地猎人发现,回归故里。我们开车近一个小时就到了他当年居住的草泊村,但我想当年也是感觉很远的,莫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骑车去拜访这位传奇人物,并与之同住一室,近距离观察他。这个人物作为变形屡次出现在《红高粱》、短篇《人与兽》、《丰乳肥臀》当中。还有,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的高密县令曹梦九,当地有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曹梦九出现在《红高粱》,出现在《丰乳肥臀》,出现在《檀香刑》中,从中可以看出从最初的比较贴近人物,到后来渐渐地脱胎变形,加入作家更多的个人创造,这样一个过程。

▌贾平凹与乡人
许多这样的作品中的细节,以及所接触到的当地人的性情都可以一一对应上。在陕南棣花的集市上,我看到两位八十多岁的老爷爷,颤颤巍巍,手拉手走路,一问才知,他们壮年时曾经一起在一个修路工地上劳动,是好朋友。这样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可以得到验证。苏北水乡,水道纵横,我们开车两个多小时从兴化到中堡,到陆王庄,当年划船可能要走一整天,那么,毕飞宇少年时随父母从杨家庄,陆王庄,中堡,各个村庄经历辗转,水乡貌似流通却封闭,《平原》中的“远方”对他意味着什么就很真实。

▌《文学的故乡》海报
2017年10月31日,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完成对莫言先生的完整采访后,我从心里已经感觉这件事在我这里结束了。2018年5月初,知道这个片子最终制作完成的时候,感觉一头笨重的母象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这孩子的美丑都不重要了,但它一定是有益的,因为从开始我都是以一种清净心在工作,希望这是一次对中国文学的致敬,希望它能给善于倾听和观看的人带来一些裨益。
这里要说,这一命题是张同道老师提出来的,而我的所有工作是在张同道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参与其中,我是幸运的,也时时刻刻都在祈愿这个片子能够顺利圆满地结束。(本文作者系《文学的故乡》文学策划。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