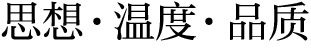2020-07-23 14:15

▌刘震云
我从小是外祖母给养大的,她现在去世二十二年了。原来我们这个院子有一棵特别大的枣树,通过这棵枣树能爬到房顶上去。1995年我外祖母去世的时候,这棵树也干枯了。
外祖母一辈子扛长工,到任何一个东家家去割麦子的时候,因为平原,那个麦趟子特别长。晚年我问过她,我说你为什么割麦子割得比别人快?还割得那么好?她说其实我不比别人割得快,仅仅是因为我要割麦子的话,我只要扎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头一回腰就会直第二次和第二十次,在别人直腰的过程中,我割得就比别人快。
故乡对一个人最大的影响,首先是语言,其次就是饮食, 当然比这更重要的是,这地方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的态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村离黄河不太远,这个地方从历史来讲一直兵火连接。另外就是旱灾。我八个月大的时候,外祖母从县城把我背到了这个院子里。县城距这儿有四十里路。她生前跟我说,我趴在她的肩膀上,路边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下了。我外祖母就上去摇他,但他已经断气了。临死的时候他要维持自己的尊严,就是把他的草帽盖在了自己脸上。他的体力就剩下这一个动作,但是他确实还处理了自己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当这种严峻的事情发生得太多的时候,如果你用严峻的态度来对付,那确实就像拿一个鸡蛋来撞一块铁一样。但是当你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严峻的现实的时候,可能幽默就变成了大海,然后这个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冰凉的现实到了幽默的大海里,它就溶化了,这是河南人幽默的来源。
我们村里,跟我同代孩子里相比,我是最笨的一个。我当时在当民办教师,好的学生确实特别聪明。有的家里穷。《塔铺》里我写过那些细节。塔铺西边有一条小河,那时候我也是两拳空空,面对偌大的世界,我不知道世界往何处去,也不知道我能往何处去。我就拿着书到玉米地里去复习。
去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农村的姑娘,一人在那水边梳头发,是长发,她在梳头的时候,前面用手拿着个镜子,晚霞既落在河水里,也落在镜子里。她的脸是红的,这个画面对我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我没走近,不知道她长得怎么样,但我觉得一定特别美。美的姑娘,美的河水和晚霞,在美的镜子里面相互映照。而像这样一个镜头,在世界上转瞬即逝,没有人在乎。她也忘了,世界也忘了。但是确实世界因为有这一幕变得特别不同,这些不同组成了世界,组成人性灵魂里那些柔软和温暖。
一个作者应该表达自己的情感跟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个写作才是有趣味,有意思,并且有意义的。当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也应该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时候,河边这一幕它对激发我写《塔铺》,是非常重要的。
农村的天黑跟城里的天黑不一样。城里的天黑是由上往下黑,接着城市的灯就亮了。农村不是,它是从庄稼地里开始黑。农家的孩子往村里回的时候,他走得特别远,但因为农村周边比较安静,他们谈话的声音,还能回响和传到你的耳旁。
像这样的情形,包括这种声音,这种背影,从庄稼地里往上黑的这种气氛,有时候在世界上可能非常不重要,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我在深处听到这种声音,身处这种氛围中间,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当我成为一个职业作者,我觉得可能它们在世界上特别珍贵。(文字与图片素材由《文学的故乡》摄制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