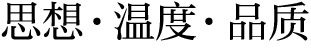2020-07-13 15:50
西苑是明代重要的皇家园林,因在北京紫禁城之西而得名,其范围四至,大致是东至西苑门,西至西安门,南至长安街一线,北至北安门一线,主体区域在宫城西墙和皇城西墙之间。
1368 年,北伐明军逼近元大都,元顺帝弃城北遁,从此直到1644 年,北京都是大明王朝皇冠上最璀璨的那颗明珠。在这二百七十六年中,有十四位皇帝,无数的妃嫔和王侯将相在此上演了一幕幕喜怒哀乐的剧集,而西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舞台。
洪武三年(1370),朱棣受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之藩北平,从此就和这座城市结缘一生。朱元璋驾崩、建文帝登基后,朱棣暗蓄力量准备谋反,广蓄奇人异士,得到姚广孝(道衍)等谋士相助,仗着燕王府乃是元故宫,有深邃宫墙的优势,“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zhòu)翎甋(dì)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明史·姚广孝传》)。此处明言练兵在“后苑”,再者蓄养鹅鸭需要水面,则此“后苑”为接近太液池的西苑无疑,可以说广阔又隐蔽的西苑在朱棣起兵初期助了他一臂之力。朱棣即位之后,在营建北京、拆毁元故宫新建紫禁城期间,西苑还临时承担起了皇宫的职能,永乐十四年(1416),“八月丁亥,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宫为视朝之所”(《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九)。西苑中新营建的西宫的位置就在元代隆福宫和西御苑的旧址上。

明代紫禁城与西苑位置略图(来源:侯仁之《北京紫禁城在规划设计上的继承与发展》)
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后,紫禁城作为帝国政治核心的地位完全确定下来,西苑更多地保留了其离宫别苑的功能,常作为君臣游乐之所,史书中多有此类记载,如宣德三年(1428)三月:
命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夏元吉、杨士奇、杨荣等及翰林诸臣凡十八人从游西苑、万岁山,诏许乘马,中官导引,登山周览,复赐登御舟泛太液池。上谕诸臣曰:“今天下无事,虽不流于安逸,而政务之暇命卿等至此,以开豁心目,庶几古人游豫之乐也。”(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一七)
但自此时起,西苑除了供游幸之外,又多了“高墙”和“冷宫”的功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犯法的藩王、妃嫔乃至帝王往往会被囚禁到此处。如宣德元年八月,太宗次子汉王朱高煦反,宣宗御驾亲征至其封地乐安,逼降高煦,押送北京,“锢高煦于西内”(《明史·宣宗本纪》)。后高煦终以桀骜不法被烧死在此。再如弘治五年(1492),荆王朱见潚因“戕害骨肉,渎乱人伦”被逮治,孝宗念及宗亲之谊从轻发落,“削王爵降为庶人,锢之西内”(《明孝宗实录》卷七〇)。
汉王、荆王不过是犯了法的藩王,西内还囚禁过失意的帝王。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中英宗皇帝被瓦剌军队俘虏,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在大臣拥护下登基称帝,是为景泰帝。后英宗被放归南还,被尊为太上皇,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病重,其兄太上皇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支持下“夺门”复辟,重登九五之后,朱祁镇立即对自己的弟弟下手,“废帝为郕王,迁西内”(《明史·景帝本纪》)。不久,景泰帝暴崩于西内,后人有猜测为英宗派宦官勒死者,至亲兄弟手足相残落得如此结局,令人不胜唏嘘。景泰帝死后,朝廷赐谥号曰“戾”,毁其寿陵而以亲王礼葬金山以示减煞。至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顾念叔父“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之功,恢复其皇帝之号,并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王绂,《北京八景图》卷之《太液晴波》,明,纸本水墨,42.1×2006.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或许正是因为宪宗常怀宽仁之心,也是在成化十一年,老而无子的他竟然收获了一个已经六岁的皇子,此事细细说来曲折婉转不减小说,而其发生之地即在西苑。大概六年前,宪宗偶然临幸了一个典守内藏的女史纪氏,纪氏乃广西土官之女,被俘获充入掖庭,未曾想偶遇宪宗答对称旨,遂得恩幸,珠胎暗结。彼时万贵妃专宠,后宫女子有孕者全被逼堕胎,万贵妃听闻纪氏有孕,令婢女去逼纪氏堕胎,婢女可怜纪氏,“谬报曰病痞,乃谪居安乐堂”(《明史·孝穆纪太后》)。
明代安乐堂有二,一在北安门内街东,为宫人杂役养病所居,“凡在里内官及小火者,有病送此处医治,痊可之日,重谢房主,消假供职”(刘若愚《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一在西苑内金鳌玉桥西羊房夹道者称内安乐堂,“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发此处,待年久再发外之浣衣局也”(同上)。纪氏所居者即为此处。后来纪氏生下一子,幸得宫人掩护才得存活,时废后吴氏亦居西内,“近安乐堂,密知其事,往来哺养”(《明史·孝穆纪太后》)。皇子潜养西内长至六岁始为太监张敏奏知宪宗。宪宗大喜,父子相认后以得子昭告天下,将纪氏移居西内永寿宫,但不久纪氏暴薨,后人认为极有可能是万贵妃下的毒手。纪氏母子在西内历尽艰辛,纪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子最终被立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孝宗皇帝,纪氏亦被追尊为皇太后。

1922年的金鳌玉蝀桥,此桥原为木桥,弘治二年改建为 石桥,新中国建立后拓宽道路,拆除了东西两端的牌坊,金鳌玉蝀桥是北海与中海的分界线。
对孝宗而言, 西苑是其“ 潜龙”之地,幼年艰辛苦难皆与此地相连,但到了其子武宗之时,却将此处变成了逸乐骑射之地。正德二年(1507) 起, 武宗在西苑费银二十四万馀两新建豹房二百馀间,广蓄美色与义子、番僧等人,日日声色犬马,不再回归大内。武宗在豹房乐不思蜀又多信用狡黠之徒,亲昵逾常人,如江彬“出入豹房,同卧起”(《明史·江彬传》)。而诸宵小也引诱武宗以玩乐为急务,江彬知道武宗自幼爱好骑射,于是进言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号“外四家”,由江彬统率练兵西内,“帝自领群阉善射者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明史·江彬传》)。上文所言检阅骑射之“平台”亦因此而建。好在爱折腾的武宗享寿不长,三十一岁就驾崩于他流连忘返的豹房,遗诏兴献王长子嗣位。孝宗、武宗父子二人一生于斯,一终于斯,生死枯荣皆与西苑结缘,而从此之后,帝系转入兴献王一脉,大明王朝的历史即将翻开全新的篇章,而西苑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接替武宗即位的是其堂弟朱厚熜, 即后世所言的嘉靖皇帝。嘉靖帝以外藩入继大统,因为“大礼议”事件政局多有动荡,嘉靖年间进行礼制改革,其中亦有在西苑施行者,且自嘉靖二年(1523)起,皇帝供斋醮神,建殿设坛多在西苑,但这些还不足以表现皇帝对这座园林的喜爱,真正让嘉靖帝和西苑生死相依还要等一件大事的到来。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在宫中不堪凌虐的杨金英等十多位宫女趁着嘉靖帝熟睡,用绳索勒住其脖颈,意欲杀之,但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而失败,事后诸宫女皆被凌迟处死,此即明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嘉靖帝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虽说化险为夷了,但是从此疑神疑鬼,总以为宫中不宁,“疑壬寅大变,内有枉者为厉”(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在这种恐惧心理作祟下,嘉靖帝“益厌大内,不欲居……决计他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其迁居的地点就是西苑永寿宫。永寿宫是永乐帝为燕王时的旧宫,正是世人所言的“西内”核心区域,祖宗龙潜旧邸甚符合嘉靖帝的要求, 但嘉靖帝入住永寿宫之后,便不再视朝,时人称其“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明史·陶仲文传》)。当然,作为一国之君是不可能完全不理政事的,于是嘉靖帝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选择亲信的勋戚大臣入值西内,将西苑无逸殿左右厢房辟为“直庐”,供值班大臣起居, 以便有事及时征召,严嵩、徐阶等内阁重臣皆享受此等待遇。内阁大臣办公的地点移到了西苑,皇帝重要令旨皆自西苑出,此时西苑反而取代紫禁城,成了帝国的政治中枢。

《御花园赏玩图》,局部,明,绢本设色,36.7×690厘米,私人收藏
嘉靖帝避居西内是为了玄修和躲避紫禁城的“厉鬼”,宫中看似安定下来,但是“壬寅宫变”的馀波仍未平息,五年后在西苑发生的另一件事又彻底改变了后宫的政治格局。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不慎失火,殃及方皇后寝宫,“中官请救后,上不应,后遂崩”(何乔远《名山藏》卷三〇《坤则记一·方皇后》)。嘉靖帝如此冷血无情仍与“壬寅宫变”有关。宫变当天方皇后闻知凶信赶来救驾,在捉拿与事宫婢的时候趁机将无辜的曹端妃和王宁嫔牵连进来,此二人皆是嘉靖帝宠爱的嫔妃,尤其是曹端妃聪明漂亮甚得皇帝欢心,是方皇后在后宫的劲敌。方皇后趁嘉靖帝病悸不能言,快刀斩乱麻将端妃、宁嫔同磔于市。事后嘉靖帝自然不无怀疑,但又无证可查,现在得此良机能为宠妃雪冤报仇,自然也就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隔岸观火了。方皇后是嘉靖帝的第三位皇后,其死于非命后嘉靖帝再未立后,后宫格局为之一变。嘉靖朝其后二十年六宫无主,皇帝连正妻都没有一位,身边少了许多勾心斗角,一心向道的皇帝终于可以专心玄修了。

元大都城皇城内的太液池(来源:侯仁之《论北京旧城的改造》)
嘉靖帝表面上看着虔诚修道,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净模样,其实也都是些骗“鬼神”的伎俩,兹举两事以证其虚伪。其一,嘉靖帝因“事玄设醮,不茹荤之日居多”,所以常要吃素,但锦衣玉食惯了的皇帝对寡淡的素斋哪能下咽,宦官揣摩圣意,“茹蔬之中,皆以荤血清汁和剂以进,上始甘之,所费不赀”(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御膳》)。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虚假玄修,纵有神仙在上也不会降福于他吧。其二,清修之中,花天酒地丝毫没有耽误,这位一心向道的皇帝于酒色无一不沾。嘉靖四十年十一月,永寿宫被一场大火焚毁了,而起火的原因竟然是“上是夕被酒,与新幸宫姬尚美人者,于貂帐中试小烟火,延灼遂炽”(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万寿宫灾》)。其荒唐可见一斑。
西内这场火本是嘉靖帝骄奢淫逸引起的,但谁又能料到恰是西内这场火给大明朝烧出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朝局。永寿宫焚毁后,嘉靖帝暂居玉熙殿等处,但是皆狭隘潮湿不宜居。其实嘉靖帝对于住了二十年的永寿宫甚有感情,内心是很想重建的,便假借宫殿不宜居之事向首辅严嵩咨询该如何办,但此时严嵩已然老迈迟钝,又无其子严世蕃在一旁协助,匆忙应对竟然建议皇帝暂居东华门外的南宫,南宫乃是英宗北狩回京时所居之处,是“逊位受锢之所”,因此犯了喜欢祥瑞的皇帝的忌讳,嘉靖帝听闻此言对严嵩甚是不满。此时善于察言观色的次辅徐阶抓住机会建议重建永寿宫,并美其名曰重建是利用建设三大殿的“馀料”,替皇帝完美遮掩了过去。徐阶又推荐精明干练的工部尚书雷礼主持重建工程,三个月后就把一座新的宫殿建成了,嘉靖帝龙颜大悦,赐新殿名为“万寿宫”,又奖励功臣,徐阶加官少师,兼支尚书俸,荣宠已经超过严嵩。徐阶又趁热打铁联合道士蓝道行,让其在西苑扶乩之时伪造乩语指严嵩为奸臣,至此嘉靖已有去严嵩之意,御史邹应龙闻知此事立即飞疏弹劾,公议顿起巨浪,群情汹汹已不可挡。至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严嵩罢相之诏下达,六月二日,盘踞朝野二十馀年的严阁老黯然离京,一个时代落幕。严嵩以议礼起家,又在西苑内伴随嘉靖帝修玄二十馀年,亲撰青词,身试仙丹,无一不小心谨慎以固其宠,却不想荣宠在西苑而极、亦在西苑而衰,自是一番轮回造化。沈德符曾评价严嵩曰:“分宜一生以逢迎称上旨,独晚途片言稍逆,顿失权宠,岂天夺其魄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
严嵩被逐, 日薄西山的嘉靖朝时日也所剩无几了,但嘉靖朝对明王朝影响深远,尤其是其历时四十五载,之前诸帝无一能与其并肩者。而且即便是放眼整个大明朝,若论享国长久能和嘉靖帝相提并论的也只有其孙万历皇帝,而万历朝历时四十八年,对国家影响之深更甚于前朝。而且万历朝和嘉靖朝一样也有一件扰动朝局二十馀年的大事,即“争国本”。“国本”乃是太子之谓,取储君乃社稷根本之意。明朝立储基本遵循“立嫡立长”之制,但到了万历朝立太子之时却出了麻烦,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欲立其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而大部分朝臣却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两派势力拉锯之下致使东宫储位久久不决。在这场角力赛中,大高玄殿又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原来在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浓情蜜意的“热恋”期,曾经仿效唐明皇杨贵妃长生殿故事在大高玄殿起誓,约定立福王为太子,明人对其事记载颇详:
郑贵妃身负盛宠,福王生,即乞怜神庙,欲立为太子。北上西门之西,有大高玄殿,供有真武香火,颇著灵异,神庙偕贵妃特诣殿行香,要设密誓, 因御书一纸, 封缄玉盒中,贮贵妃处为信。后廷臣敦请建储,慈圣又坚持立长,神庙始割爱定立光庙。既立,遣使往贵妃处取玉盒来,封识宛然,启盒而所书已蚀尽,止存四腔素纸而已。神庙悚然怀负誓之歉,从此二十年中不复诣大高玄殿。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从此记载看,万历帝一开始对于立福王一事很是坚决,所以才敢在大高玄殿真武神像前与郑贵妃盟誓,但未曾想神灵不佑,一场海誓山盟的约定却毁在了小小的蠹鱼口中。但立储一事的失败对万历帝的触动是巨大的,其影响从伤心之地大高玄殿波及帝国广阔的天地中,“天子”在神灵前面的誓约都作不得数,最后败给了一群叽叽喳喳的臣子,看来做皇帝也不能事事如意。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对国家政事也意兴阑珊,不再留意朝政,荒怠之局渐成。外朝大臣们在为这场“正义”的斗争胜利欢呼,但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此事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争国本”与其后不久发生的“妖书案”、明末三大案都有密切关系,国家又在争吵中日渐衰弱。而朝臣之间党争日趋激烈,东林党与齐、楚、浙诸党以及之后的阉党的斗争几乎将国家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古来史学家尝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大明朝就像这座日渐荒废败落的西苑园林一样,静静地等着最后的崩塌,等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明·商喜,《宣宗行乐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万历皇帝去世之后,一子二孙先后即位,国运日蹇,生民日艰,焦头烂额的皇帝很少顾及西苑了,西苑渐渐远离了帝国的政治和权力中心,回归到了一座宁静自然的园林。二十四年后,甲申年的料峭寒风送来了帝国的丧钟声,当众叛亲离的崇祯帝在凌晨踉踉跄跄地登上万岁山的时候,在北京城这个制高点上茫然四顾,他一定看到了这座承载了大明王朝近三百年荣耀与繁华的园林。
西苑与大明朝三百年相始终,一座园林能阅尽国家大政与兴衰荣辱,亦是世间少见,而湖光山色之间斗转星移,铅华洗尽,太液池千顷碧波浪起之处,仍是那处绝佳园林。
文 |李根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原载于《文史知识》 2020年第2、3期“人文游踪”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