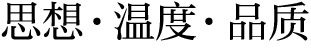2022-01-21 17:46

“王亮,内蒙古太仆寺旗人,文学硕士。曾为刀笔吏,现为火头军。”《爸爸的文学课》一书勒口上,寥寥两行字,是“文学中年”王亮的自我介绍。王亮,一个听起来普通的名字,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现在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爸爸——正如我们身边熟悉的许多人一样,但他做着一件不太普通的事情:在业余时间,坚持和自己的女儿进行有爱又别致的“文学共读”,在伴随孩子成长的漫长时间里,将文学对自己的浸润,以一种亲近的方式流贯到孩子身上。

这些关于文学共读的文章,王亮断断续续贴在网上,如今汇成了一本书。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他称之为“小册子”,质朴里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关于文学,关于家庭,关于教育,关于爱,它们藏在字里行间,藏在父亲和女儿的童真不失哲思的对话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内部如何通过读书建立起亲密的、文学性的亲子关系。

沉浸阅读的“火头军”
与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不同,王亮的“爸爸文学课”,是个人性的,甚至有一点私人性的,比起何种“目的”,单纯源自他对孩子的爱和对文学、阅读的情缘。沿着他并不算复杂的经历回溯,会发现这份情缘久已内化在他的生命经验中。
王亮的故乡在内蒙古距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小镇,他相当诗意地描述说,“南面是草原,北面是戈壁,春夏短暂,寒冬漫长。至今我对故土最深的印象依然是漫无边际、点缀着玻璃酒瓶碎片、因混杂灰尘而呈灰黄色的雪原。”高考时,他像所有小镇青年一样,向往着离开故土,越远越好,于是报了分数段内最远的云南大学。本科时听从家里意见,学了一个并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前决定跨系考研,才报了心之所向的中文系。
回忆起在云大中文系读研的日子,王亮觉得那是人生中最重要和最愉快的三年,几乎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和周边书店中度过的。书店里经常遇见中文系的老师们,会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感想。给他触动最大的是遇到赵仲牧先生的情景,赵先生当时还健在,已是古稀之年,却依然拄杖躬身屹立于书架之侧,翻阅最新出版的文史哲类书籍。王亮见之似有所顿悟:一个人应该去追寻自我完善,无论年龄和际遇。多年后,他总结自己人生最大的理想,依然是“做一名始终保持热情、心无旁骛沉浸于阅读之乐的普通读者”。
毕业后,漠北人王亮留在了西南昆明,工作,定居,转眼二十余年。他先后做过电视台记者、杂志编辑,后来进入机关单位从事办公室工作,近两三年主要负责管理单位的职工餐厅和其他物业,正如个人简介中的戏言,从“刀笔吏”成了名不副实的“火头军”。尽管离开学校多年,工作十分忙碌,他也从未让文学离自己远去,依然坚持阅读、写作,以此抵抗庸常生活给自己造成的“内伤”。
2012年,女儿之月出生,改变了王亮的生活。读书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他只能塞一本诗集或散文集在包里,随时利用碎片时间读上一小段。但伶俐的女儿很快让他从做爸爸这件事中获得了新的乐趣,那就是和女儿一起读书,他愿做一个蒙台梭利所说的“聪明的有修养的向导”,将她引入他所热爱和依赖的精神世界。

王亮女儿王之月酷爱画画,王亮也鼓励她把文学作品画下来。之月画的这幅《美丽,并不孤独的火车》,灵感源自和爸爸共读的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诗歌《火车》。
让文学与经验相认
王亮回忆起来,有意识地陪女儿共读,是从她5岁开始的。那年,王亮给她买了一套“世界文学大师绘本”,其中有一册是拉美文学爆炸代表人物之一科塔萨尔的《熊的话》。读完之后,女儿一度热衷于去卫生间听水管里的“管道熊”有没有动静,让王亮觉得很有意思,父女俩从阅读赋予的想象中获得了无穷的欢乐。
和女儿共读时,王亮起初也是读给女儿听,像多数家长一样,但不知不觉间,“文学中年”的属性就流露出来。他总忍不住夹带一些“私货”,不仅以新的方式来重新讲述《静夜思》《江雪》等熟悉的作品,还带女儿“造访”了卞之琳、汪曾祺、吉卜林、特德·休斯、里尔克等离小孩子稍微“远”一些的作家,只要不完全脱乎儿童的理解和认知经验的作品,都会被他介绍进来,成了还在上小学的女儿的文学课材料。
一篇篇阅读王亮给女儿的“文学课”,时常让人莞尔。这位“爸爸老师”,不是一板一眼地说文解字或传达何种“意义”,而是亲切地调动着一个小孩子所拥有和理解的成长经验,开启她的情感通道,从中寻求与纸上文字的共鸣。读由余光中翻译的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名诗《火车》时,他和女儿探讨为何“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起初女儿不解,他耐心描述起一家人上次在火车站送别外公的情景,还有幼儿园毕业时全班小朋友不管关系远近一起哭起来的情景,让她逐渐体会到这是一种送行人的“共通”的情感体验。疫情隔离在家时,他则会给女儿讲杜甫的《江村》,在老杜“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对草堂日常景象的描摹中,隔着一千多年,一同体会在风暴眼中,家庭、家人的珍贵与相互依赖之处。
正如王亮自己的经历,在引导女儿进入文学时,他很重视这种文学与生活、与自我经验的联结。他讲起一件事情:女儿刚上小学时,他曾拿起语文课本翻看,第一册第一页赫然印着一首对韵歌: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今古。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本应是由熟悉逐渐拓展到陌生,但语文教育似乎背道而驰,“为什么要从如此抽象的表述,而不是孩子们身边的事物开始呢?比如学校、课堂、老师、同学,哪怕是一支粉笔、一张课桌呢?”王亮始终觉得,唯有把个体的经验与文学作品相体认,文学作品才会对“我们”具有意义,而也正因为一代代读者的参与,把他们的情感与思想“寄托”在文学作品上,它们才能不断焕发生机。他做了一个精当的譬喻:“陈列在博物馆的艺术品固然美丽,但很多却丧失了其现实基础,成为了供我们瞻仰的标本,唯有那些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事物,才真正具有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他带女儿读的每一篇作品,都因加入了当下时空里父女俩的交谈、玩笑和解释,而构成新的文本。
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因王亮自己工作繁忙、女儿学业紧张,留给“文学课”的时间并不丰裕——这从他更新文章的频率也能看出来,因此他常常选择的文本是诗歌、散文和故事。尤其是诗歌,占了绝大篇幅,从骆宾王的《鹅》到里尔克的《预感》,不拘古今中外。这也和王亮自己对于诗歌的阅读偏爱有关。
虽然是给小学低年级的女儿“讲课”,王亮却毫不敷衍,认真“备课”,将女儿看作是可以平等对话、甚至给他启发的对象,带她从文本表面进入更深阔的文学场域和文化背景。因而尽管是面朝女儿,从一般的视角看,王亮对诗歌的解读也相当有洞见。譬如讲《江雪》,王亮找来《渔歌子》和《楚辞·渔父》、姜子牙和严子陵钓台故事等与之对读,让女儿初步理解“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化意境中的象征意味。或如讲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除了另外一些古代送别诗外,他还“动用”了尧十三的《雨霖铃》(改编自柳永词)、陈鸿宇的《别送我》两首歌作为辅助材料,在这些文本的交互中,让女儿渐渐体会出属于中国人的送别的情愫。
王亮爱好古诗词,但对所谓“传统文化传承”,有他自己的观点。女儿学校发国学讲座通知,他看了看宣传,开给孩子的书单里竟然有《太上感应篇》和《黄帝内经》,觉得不靠谱,干脆选择放弃。在他看来,随着时间流逝,古典文学文化已经有些“矿化”,“燃点”更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让它重新绽放光热,而这艰苦的工作应是成年人的责任,而不应成为年幼孩子的重担。这和他在这本书序言中所讨论到的“亲子读书”的问题有异曲同工处:在今日的读图和视频时代中,成年人选择了更简单直观的捷径,却让孩子去“开卷有益”,走一条更艰难的路,很难有说服力。因此王亮的文学课,正如他在网上所说明的,是他在自己身上、在自己家庭内部所做的一种“实验”,从具体的问题和方向,探索教育的一种可能性。
开始上“爸爸文学课”时,王亮女儿刚刚上一年级,现在已经十岁了,可以自主看《哈利·波特》和《魔戒》,父女俩之间也渐渐由共读变成了独立阅读之后的讨论。王亮说,他的书架从来都是对女儿开放的,只要感兴趣,她可以随便从上面抽出书来读。这个寒假,女儿看上了爸爸书架上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集》,要和爸爸一起读。这本诺奖获得者的小说比较风格化,对小学生来说并不算友好,王亮觉得“颇有挑战”,但转念一想,既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何妨一试呢。“爸爸老师”唯一要做的,是对阅读材料适当挑一挑、分分级,以免太出乎孩子的经验和理解。
中文系出身的王亮,没有成为职业作家或诗人,他给孩子上“文学课”,也并不抱怀这方面的职业性目的,只因他相信文学属于广泛的大众,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只要人类还在使用语言,需要彼此交流或有表达的诉求,文学就会存在和发生,或隐或显地环伺在我们生活周围。”王亮说,他自己曾经从文学和阅读中获得滋养,因而,也愿他的孩子通过阅读和学习文学,能够更加独立、更加尊重人性、更加体会生命的美好。
给孩子更丰富宽广的文学世界
书乡:您和孩子共读文学,选的大多数文本都是诗歌。在您自己的阅读经验中,诗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特别注重用诗歌来进行对孩子的文学教育?
王亮(《爸爸的文学课》一书作者):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诗歌篇幅相对短小,当时我女儿年龄还小,孩子的专注力很难持续特别长的时间;二来确实和我个人的阅读有比较大的关系,我热爱诗歌,自己也曾尝试创作过一些不成熟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诗歌最能赋予语言文字以美感,一句话或一种情感以诗的方式表达,就让人觉得美、觉得深刻、觉得恰如其分,比如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烦心事,但李煜却能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真是又准确又美好。具体到孩子,我想诗歌作品有助于激发孩子的想象力,丰富孩子的情感体认,增加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角度。
书乡: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专门给孩子的诗歌选本(如金子美铃、谷川俊太郎等,还有一些孩子自己写的“儿童诗”),注重童真、可爱、灵感这一面。但您显然覆盖面更广,里尔克、特德·休斯等这些象征意义比较浓的也都选来给女儿讲了。所以给孩子讲诗,选择标准是什么,您侧重诗中传递什么样的内容?
王亮:我觉得市面上很多打着“给孩子”的作品选集都严重低估了儿童的认知和心智能力。我个人很喜欢金子美铃、谷川俊太郎,但再好吃的菜,天天吃也会腻烦。我认为孩子的潜力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很多文学经典作品,只要稍加引导,他们都是可以理解和体会的,我愿意把一个更丰富、前景更宽广的文学世界介绍给我女儿。同时,某些作家适合儿童阅读,某些作家不适合儿童阅读,有时候也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刻板印象,比如特德·休斯,在我看来他和他妻子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些诗因为意象的明晰和强烈,想象力的丰富和奇崛,就特别适合讲给孩子,而且他本人也确实有此想法,专门写过一本诗集,名字就叫《写给你的诗,孩子》,里面每一首诗单列出来都是一篇古灵精怪的童话故事。他还做过大量诗歌阅读与赏析的普及工作,我在书中的一些灵感就源自他的广播电台诗歌公开课《诗的锻造》。
我觉得只要不超出儿童认知与经验范畴,都可以拿出来和儿童分享。当然,可能因为我的专业,我读的东西比一般父母多一些,选择范畴会广一些,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是作为讲述者的父母、老师真正理解了作品,真正能讲出它的好,能把对这些美好的热爱传递给孩子,唯有如此,讲授才可能是有效的。
书乡:现在大多孩子从刚一说话就学背古诗,很多人会觉得,不用太在意每个字句的意思,先让幼儿感受一下诗歌的音韵节律之美足矣。也有人(包括您)认为应当先理解诗歌,并且您还不是笼统释义,而是透彻讲解。所以您对社会上普遍的这种早早背诗的潮流是怎么看的?给孩子详细地讲解一首诗,会有损想象力吗?
王亮:背诗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诗歌的韵律可能比其内容具有更广泛的意蕴。但我觉得如果完全指望这种方式能让一个孩子热爱诗词或文学,乃是一种广种薄收的赌博行为,行与不行,完全看机缘,否则只是增进了孩子的语感。
在文学认知方面,我觉得很多人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文学作品不能分析研究,乃至不能讲,好像它们都是些珍稀的易碎品,一捣鼓就坏了。文物可能是这样,幸好文学艺术的载体是价格低廉的纸张,研究、分析、讲一下无损于艺术品本身。真正的文学批评也是需要巨大想象力注入的,是与文学创作不相上下的脑力劳动。
书乡:书的最后一章是关于教女儿写作的,有意思的是,您没有用学生范文来教她,而是用各种优秀文学作品来做示范。让小朋友学习汪曾祺、吉卜林等大作家,会不会觉得把目标定得太“高”了?有时候觉得您真是挺严的(笑)。
王亮:确实,我有时也在反省,我是一个有些强迫症倾向的人,凡事都希望尽最大努力做到最好,有些要求提给孩子可能的确有些严格。但作为范文,我觉得我的选择没有问题,现在市面上到处都是“给孩子”专用品,吃喝拉撒一应俱全,唯独文学阅读与写作,提供的是一些并不出色的替代品,有些甚至还相当糟糕。汪曾祺与吉卜林在我看来都写了大量可称之为儿童文学的作品,汪老先生很多作品里有着未泯的童心,读来可爱,而吉卜林更不用说,《丛林故事》改编过多版的动画片。
书乡:看到您在书中对学校的写作教学偶有微词,您觉得主要问题在哪里?
王亮:最不满的可能有两点:一是假大空,我们教育孩子在生活中不能撒谎,却在写作层面纵容乃至鼓励孩子说假话、大话、空话;二是陈陈相因,用一些取巧的陈规和套路取代真正的写作训练,千人一面。
书乡:前几天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在去年的童书品类销售中,科普类图书超过了文学类,跃居第一位。看到这本书中偶尔也有提到其他学科内容,好奇在你们家里,孩子的阅读是怎么分配的?
王亮:和把文学与生活联系起来一样,我也希望能把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在一起,因为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是因为我们看待和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了区别。我觉得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对于一个人同样重要,犹如鸟的双翼,缺一不可。只有科学知识,而没有文化艺术修养,人就容易呆、木,缺少趣味;相反,人就容易空、浮,华而不实。在我家里并不存在阅读的分配,一切以兴趣为依据,想读什么读什么,想怎么读就这么读,只要她想读,我从来不做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