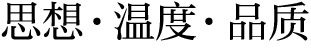2021-04-09 21:22

今年是日本诗僧、书法家良宽辞世190周年。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在其题为《日本的美与我》的获奖演讲中,引用了良宽的辞世和歌“我有什么遗物/留给你们?——/春花,山中/杜鹃鸟鸣,/秋日红叶……”,以及另外三首短歌——“长长的春日,/跟孩子们/玩手球——/啊,一天/又过去了”、“风清,月明,/我们一起/尽情跳舞吧,/让老年的余波、/余韵永荡……”、“我并非不与世人/交往:是因为/我更喜/爱独/游”,以此来说明良宽的诗歌如何体现日本的精髓以及自古以来日本人的情感和心性。
川端康成说:“这些短歌反映了良宽的心灵与生活。他住草庵,穿粗衣,漫步原野道路与儿童嬉戏,和农夫闲聊,不用艰难的语言,不高谈深奥的信仰与文学,而全然以‘和颜爱语’——纯真无垢的言行相对。他的诗歌和书法,皆超脱了江户后期,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日本近世的习尚,而臻于古代的高雅之界;直至现在,其书法和诗歌仍深受日本人民珍爱。在他的辞世诗中,他说他没有什么东西可留作纪念,也不想留下什么,但自己死后,大自然仍是美的,这也许可以视为自己留给此世的遗物吧。这首短歌凝聚了古来日本人的情怀,也可从中听见良宽充满宗教信仰的心。”
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在其《禅与日本文化》一书中也说:“认识一个良宽,等于认识日本人心中的千千万万良宽。”作为一个僧人、作为一个禅宗修行者,良宽在悟道、出师后,并未全然出世、离世,而是以“和颜爱语”回归人世,以无邪、无垢之心入世、怜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超脱虚假和人为桎梏的大智若愚者。他遗留给此世的,有一百一十多首俳句、近一千四百首和歌、近五百首汉诗,以及包括画赞、条幅、屏风、扇面、短册、汉诗、短歌、狂歌、俳句、偈语、戒语、书简等超过两千件墨宝,以及一个随性、任性,“腾腾任天真”的良宽,一颗既“良”且“宽”的天真、安贫、慈爱之心。

诗僧良宽像 安田靫彦绘
出家离国访知识
良宽(1758-1831),号“大愚”,宝历八年十月出生于日本越后国出云崎(今新潟县三岛郡出云崎町)村长山本家,为长男,幼名荣藏,十五岁成年礼后名文孝。父亲山本以南是俳句诗人,有“北越蕉风栋梁”及“出云崎俳坛中兴之祖”之称,良宽家甚富文学与宗教气氛,藏书颇丰(他的三个弟弟、三个妹妹,长大后也都或能俳句、短歌,或能汉诗)。1765年,良宽入邻町尼濑曹洞宗光照寺的寺子屋(私学馆)学习。1770年,汉学家大森子阳(1737—1791)回越后分水町开设私塾“三峰馆”授课,十三岁的良宽随其习汉学,至1775年,前后六年。
幼年、少年时的良宽聪明好学,应该随老师读过《论语》、《孟子》、《三字经》、《孝经》、《诗经》、《文选》、《唐诗选》等汉籍,奠下汉诗写作的基础,同时也涉猎了家中所藏《古今和歌集》、《西行法师歌集》、《徒然草》、《平家物语》等日本文学书,存取了日后写作和歌时的养分。据说有回盂兰盆节期间,十二三岁的良宽每晚在家中阴暗的灯笼下读书,母亲心疼,叫他去看大家跳舞,良宽不情愿地走出家门,不久母亲发现庭院石灯笼底下有人影晃动,以为是小偷,她缓步趋前,一看是良宽在读《论语》。
1779年,备中玉岛(今冈山县仓敷市玉岛)圆通寺住持国仙和尚来光照寺访问,二十二岁的良宽由其受戒,成为正式僧侣,僧名良宽,后随国仙和尚回圆通寺修习正规曹洞宗禅,也学习汉诗、和歌、茶道、花道。国仙和尚于1791年4月圆寂,秋后良宽踏上归乡之路。
漫漫返乡路上的这几年间,良宽所到之处包括关西的赤穗、明石、京都、高野、吉野、伊势、须磨等地(1791年秋至1792年春),以及四国(约1792或1793年)、关东,且可能远及陆奥地区。他一方面拜访各地“有知识”之人及同门师兄弟请教、印证所思所学(“出家离国访知识,一衣一钵凡几春”),一方面寻访前辈诗人行吟过的名胜。在大阪弘川寺西行法师墓前,他咏此歌向西行法师致敬:“原谅我,如果我/所折之花/色渐淡,香渐薄/我可献给你的/唯独我的一颗心”。
良宽大概于1796年秋返抵家乡出云崎,据说先住在寺泊町本乡的一间空屋,此阶段他有一首短歌如此写道:“回到家乡越后:/还未习惯/家乡气候,/肌肤/时时寒……”。他于1797年移往分水町国上山半山腰的五合庵居住。1802年良宽离开国上山,先后借住于其他寺庙,大约于1805年春搬回国上山五合庵定居,直至1816年才搬离到国上山山麓的乙子神社草庵。
艺术之花多面开
先后住了十多年的五合庵是半生漂泊的良宽安定或“求”安定之所——安于浮生的起伏,困惑,孤寂,不安……:“唯求/孑然独立/秋之庵”;“久住则安——/此际彷如身在/庐山阵雨中”;“何处可觅/比国上山/更让我心动的/住所——/无也!”。五合庵的“五合”指半升,人一日所需之米约五合——“五合”足矣,良宽以此明自己清贫生活之志:
生涯懒立身 腾腾任天真
嚢中三升米 炉边一束薪
谁问迷悟迹 何知名利尘
夜雨草庵里 双脚等闲伸

生涯懒立身 良宽 书
良宽在此坐禅,修行,时而下山至邻近村里托钵乞讨,与村童玩手球、唱歌同乐,与农人共饮,暇余时创作和歌、俳句、汉诗与书法——他用短歌抒发山居生活的寂寥与情意:“愁寂,但/心清澄:/日复一日/草庵/悠闲度”,“我不觉/我身贫乏——柴门外/有月/有花!”;也用汉诗吟咏之:
青天寒雁鸣 空山木叶飞
日暮烟村路 独揭空盂归
孤独隐居山中的他也时兴访友之念,或等待、欣喜友人来访:“春雨——/突兴/访友之念……”;“持美酒/与菜肴来吧,/让我一如往常/留你/草庵一宿!”。这个时期最常与他往来的文友首推昔日三峰馆同门、小他四岁的原田鹊斋医师,其子原田正贞也是良宽好友。其次是小他二十一岁,从五合庵时期到乙子神社时期持续与他密切往来,以俳句、和歌、汉诗相互唱和的酿酒商阿部定珍。
良宽的弟弟由之,继任村长时因经手款项不明被诉,后被判没收家产,山本一家从此没落,由之也于1811年剃发隐居他乡。1816年5月由之返乡,至五合庵访其兄,惊觉五十九岁的良宽衰老许多,应是反复上山、下山辛劳故,遂安排良宽于这年夏天搬到山下乙子神社草庵居住,也让良宽十六岁的徒弟遍澄(1801—1876)陪着他。兼任神社看守人的良宽笑称自己半神官半僧侣,依然淡泊、清贫,自在过日:
有人问,/就说我在/乙子神社草庵/捡拾落叶/度日……
乙子神社时期的良宽在和歌方面新获道元禅师《伞松道咏集》歌集、解说古籍《日本书纪》歌谣的《古训抄》、阿部定珍所藏《万叶和歌集校异》等书,让他更深入学习古典真髓;他边读定珍借他的《万叶集》,边以朱墨加入注记,使他自己的歌风从五合庵前半期(四十岁阶段)受《新古今和歌集》影响的“新古今调”、五合庵后半期(五十岁阶段)受《古今和歌集》影响的“古今调”,蜕变为六十岁阶段更古朴、古雅、诚挚的“万叶调”。
在汉诗方面他则延续了五合庵时期所受《论语》、《文选》、《楚辞》、《唐诗选》、《寒山诗集》等书之影响,又读破借来的九十五卷本道元禅师《正法眼藏》,坚毅其信仰、人格;此阶段良宽汉诗,益见其融儒家与佛教精神,《论语》与《正法眼藏》在胸,出家但不忘关心世事的生命与创作特质。
书法方面,自1807年开始临摹平安时代小野道风“草假名”《秋萩帖》以及怀素草书《自叙帖》的良宽,此阶段又勤学王羲之《兰亭序》、《澄清堂帖》,王献之《二王帖》,孙过庭《书谱》,怀素《千字文》等,巧化为自己书法之风,以之录写自己所作诗歌。乙子神社时期的良宽将和歌、汉诗、书法三种艺术合为一体,灿开出多面皆美的艺术之花,可说是古往今来罕见之人。

天上大风 良宽 书
1826年秋,良宽因身体状况日差,决定搬离乙子神社,于10月1日搬入岛崎富商木村元右卫门家邸内的庵室居住,在此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五年。
木村庵室时期良宽最重要的生命事件是女歌人贞心尼(1798—1872)的出现,此亦日本文学史上极浪漫、动人的一页。
至1831年1月良宽过世止,贞心尼多次拜访良宽,与他谈诗、谈道、谈心。两人关系既像一对佛门师徒,又像两位同游于诗歌之道、艺术天地的美的信徒——时而像父女,时而像兄妹,时而像知己,时而像恋人;既纯净又温润,既人性又不固着于人间的欲求、烦恼,既灵性又充满热情,既美、既真、既善又可敬、可爱。
“笨拙”的良宽
良宽生前有许多被人津津乐道的逸事。这些小故事显示了良宽的愚与真,朴拙与童心,也展现了他对儿童、庶民,对贫弱者,对花草树木的爱。他毎天早上对着天空无纸练字,或者替代纸,在土和沙上写字。用宝贵的纸练习时会练到纸全然漆黑。许多富人或相识者向他索字,良宽未必有求必应,但他却乐于为孩童写字。据说有一次良宽在燕市化缘完后,在大堤上见一群小孩准备放风筝。有个小孩拿着一张纸走来对他说“请帮我写字”,良宽问他要做什么,小孩说“我要做个风筝来放,请帮我写‘天上大风’”,良宽欣然提笔,为这孩子写下“天上大风”四个字。
良宽流传后世的书法作品中,最有名的一幅即是写了“天上大风”这四字者。这幅作品处处暴露出技法上的不完美:前三个字用墨过多,以致在刚下笔处都有宣纸晕开的痕迹;“天”的后两个笔画在用墨和力道上都嫌不足;“上”字的一竖和“风”字由上到右的勾勒都有运腕不稳的迹象;“天”字太大而“上”字太小;“风”字位置过于偏左,导致署名的空间受到挤压。
通常书法作品讲求完美技法、优雅、力度、气韵等诸多要素,但许多书法家和艺术爱好者却对良宽这幅技法不完美之作深感敬畏。良宽是技法纯熟的书法家(从他的其他作品可知),但在这幅作品中他把技法丢到一边,以赤子之心写下了不甚对称、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四个字。这质朴、孩童般的笔触,流露出的正是良宽天真、自由自在的本性。与孩童在一起时,良宽自己就是个孩童。
良宽住在五合庵时,据说有次小偷前来行窃,良宽家无长物,乃脱下身上衣服交给小偷。有一晚,小偷又来光顾,无物可偷,居然打起良宽身体下蒲团(被褥)的主意,良宽假装睡着,翻过身去,让小偷顺利地抽走被子。良宽自嘲地写了这首流传极广的俳句,感谢偷儿没有彻底搜刮一空,“好心”留下窗外月亮,让他仍富拥一室月色:
小偷忘了带走的——/我窗前的/明月
“大愚”良宽似乎从小笨到大。良宽八岁时,有天早上迟迟起床,被父亲责备。羞赧的良宽本能地抬头看着父亲。父亲跟他说:“敢直视父母亲的小孩,会变成比目鱼。”良宽信以为真,跑到海边坐在突起的岩石上,直到黄昏时被母亲找到。他告诉母亲:“一变成比目鱼,我就打算立刻跳进海里!”
单纯、善良的良宽对每个人心存敬意,遇见劳动者必鞠躬致意。他始终面带微笑,所到之处总让人觉得“严寒冬笼去,春天又来到”。

良宽与贞心尼 安田靫彦绘
受中国诗人影响深远
良宽是公认的与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并列的江户时代大诗人,除川端康成外,画家安田靫彦也是良宽的追随者之一,创作了多幅与良宽有关的画作。
良宽俳句百多首,以量而言远不及另外三人,但加上和歌、汉诗,就足与“俳句三圣”并驾齐驱了。良宽的俳句富即兴性,简洁明了,纯朴有情,不乏名句、佳句:
夏夜——/数身上的跳蚤/到天明
风携来/足够的落叶,/可以生火了
良宽的俳句颇多以古典为背景者,他尊敬古人,像《论语》里的颜回就是他一再致敬的对象:“颜回的瓢——/令人思慕的/器物!”;“下雨天——/破瓢啊,我们聊聊/古昔事吧”。良宽也很崇拜松尾芭蕉,用汉诗写过一首《芭蕉翁赞》:“是翁以前无是翁,是翁以后无是翁,芭蕉翁兮芭蕉翁,使人千古仰是翁”。
良宽的人和诗就像一个静默、灵动的水池,广纳万物,随时欢迎新元素跃入。他的和歌与汉诗(他一生中更加致力的两类诗)也同样很有亲和力。良宽一方面从不同的古典诗集、诗人处,摘取不同的词汇、诗句,混而用之,一方面又从庶民生活、大众文化中汲取养分,遣用口语与俚俗意象,让诗作更加鲜活。
“摘句聊为章”——或者说拼贴式、大量“借用”前人诗句的创作方式——是良宽诗歌一大特色,其中《万叶集》显然是良宽的最爱。良宽觉得,初学者应以质朴的《万叶集》为师。有感而发、言之有物比讲究技巧重要。
但我们不要误以为良宽只是一个复古者。《万叶集》提供他诗歌灵感,但他并非盲从地模仿,而是存乎一心地将他广泛取用的他人诗句化为己有,有效地达成一种乱中有序的谐和。
归纳几点良宽歌作特质:格调高雅;技巧凝练,内容简明浅显;凝视现实,充满慈爱之心——良宽写过一首汉诗《杜甫子美像》,歌赞因安史之乱避居成都草堂的杜甫,梦中犹忧时忧国:“怜花迷柳浣花溪,马上几回醉戏谑,梦中尚犹在左省,谏草草了笔且削”。他一定熟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且私淑、抱持这民胞物与之心:
安得广阔/黑色/僧衣袖,/大庇天下/贫穷者
安得广阔/黑色/僧衣袖,/大庇/满山红叶/免凋零
勤学好读的良宽,汉诗写作所受的影响也丰富多样,包括他自承的《诗经》、《楚辞》、《文选》,以及《唐诗选》、《白氏文集》、《寒山诗集》、《唐诗三百首》、《诗人玉屑》、《论语》、《孟子》、《庄子》、《史记》,佛典《法华经》、《碧岩录》、《维摩经》,乃至于日本的《万叶集》、《怀风藻》(第一本日人所写的汉诗选)等。影响他最大的诗人当属也是“诗僧”的唐代诗人寒山,良宽屋子里可能有一本寒山诗抄本:“终日乞食罢,帰来掩蓬扉,炉烧带叶柴,静读寒山诗……”;其次应是陶渊明,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四人。
良宽汉诗中呈现的仁义、无为、慈悲宽容等思想,兼容了儒、道、佛三教与寒山思想。他仰慕寒山的高洁,钟情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悠闲自在。良宽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应是释迦、孔子、陶渊明三者的合体。
良宽汉诗的优点在于不在乎他人对诗的定义,而能从容、灵活“抒写心中物”,和古来“诗言志”、诗乃心之声的汉诗基本理念一致,与日本其他汉诗作者大有所别。良宽以和歌抒发情感,而用汉诗表达思想(虽也不乏以汉诗吟咏情怀之作)。他的汉诗如实呈现了他的人生观、社会观,具有冷彻的观察力与宏大的想象力,饱富思想性与对人间的爱。
“身心脱落来!”
如果只能用两个字描绘良宽,我愿用“良宽”两字:良而且宽。其次我愿用“任真”:随性、任性,顺其自然。
然而良宽并非天生任真、洒脱。
良宽的个性当然有富童心、无邪的一面,但也有孤独、忧郁的一面。少年时为寡默执着的个性而苦,壮年后家族一蹶不振,这些都令人难以开朗。出家求“解”的良宽一直在练习解题、不断有惑的路上。他返乡归居五合庵,“唯求/孑然独立/秋之庵”;山间草庵中,他时感孤寂,思友、盼友至,频频想下山访友,或与世间人同在花树下(“今日,我也要/动身往春山,和/世间人同赏花”);暮年病榻上,他殷殷期盼不施胭脂的忘年红粉知己。他在人生的“求”与“无所求”之间恒久地拔河、拉扯。
良宽是经由不断修炼,“身心脱落”,而渐至洒脱、飘逸、任真之境的。日本曹洞宗道元祖师当年赴中国求道,闻其师如净禅师责骂坐在他旁边的同门:“坐禅不是这样坐的!一旦坐下,就要坐到身心脱落,坐到整个身心世界荡然无存!”道元旁听此话仿佛受电击,起身后捧香入如净禅师房,说:“身心脱落来!”
1828年11月,日本新潟三条大地震,死伤四千余人,房屋毁逾三万四千间,悲痛的良宽为此写了多首短歌与汉诗:
若我骤死/便罢——但我/幸存,要长久地/忧睹、领受/人间悲苦
良宽寄此歌给友人时,却写道:“然而,灾难来临时即面对灾难,死亡临头时即接受死亡,此乃避开灾难之妙法也”。
他也会露出这种老庄无为、顺其自然的“齐生死”双面刃。这是“任”的极致,既慈悲又残酷。
而良宽底下这首汉诗,让笔者在阅读时,真的“不觉泪沾巾”:
坐时闻落叶 静住是出家
从来断思量 不觉泪沾巾
静下来就能诗意地、俳句地、和歌地居住,任性,任真……但多不容易啊,要断绝多少惦念,一次次,一遍遍“杀”自己,一小块、一小块地“毁灭”自己,直至身心脱落,飘逸、无心。
良宽在日本之所以地位崇高,一方面是因为他汇聚了不同诗歌文类、不同古典选集与诗人的诗歌元素,让它们多层次地交错串联,以此织构出其独一无二的诗歌世界。他的诗作看似简单,其实许多都蕴含被提炼、妙化后的丰富感性。他从自身经验的诸多面向取材,以灵活新鲜的方式化用各路经典,鲜有人能像良宽这样成功融合广泛的诗歌素材,创作出质地丰美的各类佳作。另一方面,大愚、洒脱、独来独往的良宽,体现了单纯,良善,可信赖的品质,因此良宽广受现代日本人喜爱。
除此之外,还由于他是禅宗的代表性人物。不同于其他知名高僧,良宽从未建寺院、立门派、训练门徒,也无宗派之见,他遵曹洞宗自力坐禅,也随净土宗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从不说经讲道或立文字说法。事实上,他似乎刻意避免谈佛说禅。他不言传,只是“身教”。他的生活本身,他诗歌中、他书法中流露的他的性情、他的生命风格,就是最好、最高的说教。他的人生与他的艺术合而为一,以“非说教的说教”拂沐、教化人间。
良宽经常被世人贴上不同标签:怪咖,革新者,苦行僧,大愚,乞丐。许多人或视良宽为“一怪”,但良宽深深了解自己以及周遭人世,他从未排斥理性思维,神志清明,通情达理。
他是革新者,有着厌恶外在框架限制的反叛精神,但他理解顺从和虔敬的价值与自由同样可贵;他知道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但他也知道必须顺应自然,为更高、更大的和谐作出选择。
他是苦行僧,以粗茶淡饭维生,但他也明白严苛的禁食会伤身,而身伤易生歹念。
他是大愚,连孩童都喜欢捉弄他,但他其实大智若愚,“尽在不言中”是他对旁人看法的答复。
他是乞丐,大半辈子生活穷困,但在精神层次上,他也是贵族,挨家挨户托钵行乞时,他挺直身子,“心抛万乘荣”,天子的荣耀也不足羡。
良宽超越所有的定义,他拒绝片面地看待人生,他忠于那化矛盾为谐和的“大真”。人们常称良宽为“禅”师——这样的称谓似乎也还不足。他无法被界定。那天真、稚拙、自由的四个字“天上大风”,也许就是他一生最贴切的状貌。(责编:曾子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