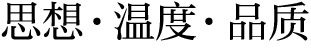2021-03-04 21:40

白导:
收到《一蓑烟雨》剧本及录像资料,十分感谢,迟复为歉。
距在繁星戏剧村现场观看演出,已有两个多月,其诗情画意、精妙雅致,让人久久难忘。今重读剧本并观看单机位录制的影像资料,更觉得无论作为戏曲作品,还是小剧场实验剧目,《一蓑烟雨》都可以说是一部别具创意和艺术特色的优秀剧目。
淑世与归隐的精神困顿
《一蓑烟雨》叙述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从忧谗畏讥、怔忡、彷徨到感悟天地、超乎尘垢的心路历程,着力表现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士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知识分子)淑世与归隐的精神困顿与人生难题。
全剧分藏、嬉、行三个段落,首尾两段均写酒、写月。借酒写性情,用月写参悟。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一到黄州,初寄寓于定慧院僧舍和临皋亭。次年,幸得友人替他从官府请得一块五十余亩的荒地,垦植略济饥窘,并筑室于此。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一蓑烟雨》的副题是“苏东坡的黄州夜色”,可见此时距苏轼来黄州已近两年。作为谴谪的罪官,苏东坡仍不免有些孤独、失落,月夜买醉,更多的是借酒忘却恶浊的官场与现实,排遣茫然、惶恐的心绪。但此时他的内心已渐趋平复,月夜漫步,放浪山水,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舒展,并在与大自然的观照中,体悟宇宙万有的妙谛。

▍《一蓑烟雨》剧照
苏轼的政治思想和态度颇为复杂。他既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多异议,对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也不完全认同,其德业文章,一生多变。他的侍妾朝云戏说他“一肚皮不入时宜”,而刘安世则称述“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元城语录》卷上)。可贵的是,苏东坡一生虽屡遭迁贬,然无论在朝在野,流转何方,始终未忘情于世,其用世之心志未因超旷之襟怀而稍有改变,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学者和政治家。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犬儒主义盛行的商业时代,在戏剧舞台上形塑这样一个立言忠直、不改其志的知识分子形象,自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和启悟作用。但我在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化用苏诗苏词的白璧微瑕
《一蓑烟雨》的舞台简约通透:八片栅栏式的立地施转隔板并列横贯舞台,在后区分隔出前后两处空间,淡淡的光晕中,人影晃动,别有韵致;旋转隔板便于检场人/角色上下场,使时空流转更为方便;运用色光变化分切空间、营造气氛,执简御繁,省简纯净;人物服饰素淡雅致,用色惜墨如金,反衬出“宋朝人”的亮丽矫逸,熠熠生辉……所有这一切,都显出构思细密,处处用心。

▍《一蓑烟雨》剧照
民族戏曲本就属于诗剧类型,唱词采用诗词体,对白也常用押韵句。《一蓑烟雨》更是大量移用苏诗、苏词,诗美与情致两相辉映;物境与心境,交杂浑成。或许有人要说,苏东坡的诗词美则美矣,但对大多数观众而言,除了觉得唱词优美动听之外,恐怕难以体味其旷逸的意趣,也难以领略其深蕴的奥义。这可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这些名句已被移入虚构的戏剧情景之中,只要与人物身份与特定情境相契合,它们在原诗(词)中的意义大可不必深究。
诗为心声,倒是这些挪用的诗句是否符合特定场景中人物的内在真实,显得更为重要。例如,第一段,苏东坡从酒馆夜归,敲门无人应答,独自到江边赏月,遇见一个青年书生(苏东坡二十年前的少年之身),两者对唱所引用的诗词,无论是苏轼寓居定慧院时所写的《卜算子》(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或是在沙湖道遇雨后所作的《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都是贬谪黄州之后的作品,超旷之怀杂有怨断之音,符合苏东坡在此时之地的心境,却与“少年之身”不合。二十年前的苏东坡,进士及第、制科出众,正当意气风发,与戴罪之身千里投荒时的复杂心境大为不同。二个不同年代的苏东坡同调对唱,彼此唱和,不若两相比对、调异而志同更为可取。
两大创造:“宋朝人”和“三个苏东坡”
将检场者转化为形象俊朗、舞姿轻捷的“宋朝人”,是此剧的一大创造。检场者/宋朝人仍然具有检场功能,只要稍加拓展,也可能构成穿插于三个场景之间的另一个“叙述层次”。一些论者在谈及古代诗词的精神史时,总喜欢区分唐音宋调。有人更将宋朝的文化当成我国古典文明的暮年。这样的区分和论述显得过分虚泛。苏轼生活的年代,党争激烈,但从经济、文化上说,即便算不上太平盛世,也属于边关相对平静、社会比较安定富足的岁月。苏轼的频遭贬废,其实只是封建时代宦海沉浮的常态。编导者略去对全剧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的具体描述,借助一个淡雅清丽、伸屈进退旷逸自适的舞者(宋朝人)形象,将一个朝代的血肉气脉既虚又实、既实又虚地象征性呈现。它超越了戏曲舞台上常见的那种娱乐性、装饰性的舞蹈穿插,在与一个饱经忧患又超然旷达的伟大诗人虚虚实实的两相映照中,历史的痛切,生命的感喟,全付之观众的想象与各自不同的读解。

▍《一蓑烟雨》剧照
三个苏东坡——少年之身、身后之身与现实的苏东坡——在同一场景现身,也是戏曲艺术(戏曲表演)的一大创造。文艺作品中分身人的出现,最初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双重性格。早在十九世纪初,爱伦·坡在其《威廉·威尔逊》中,就将分身术运用在小说之中。戏剧方面,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是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用同一个演员当众换装,扮演善良的妓女沈黛和她凶狠的表哥隋达,表现人性善恶的滑动,揭示滋生人性恶的社会根源。1991年,美国作家爱德华·阿尔比在其剧作《三个高女人》(香港话剧团2014年12月曾在香港艺术中心寿臣剧院演出过此剧,导演David Kaplan)中,让一个女人26岁时的自我、52岁时的自我和92岁时的自我,出现在同一戏剧场景。在三个高女人的不断龃龉、争辩中,展现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处世态度与内在心境的变化。《一蓑烟雨》对分身人的用法,同以上三者均有不同,尤其是末尾三个苏东坡载歌载舞,穿山越水,共赴险阻,极富我国文学想象与艺术实践中特有的抒情意味。对三个苏东坡同框的得失成败,容或有不同评价,但这无疑是当代戏曲借鉴、改造现代/后现代舞台技法的有益尝试。
传统戏曲如何现代转身
戏曲界谈论继承与创新已谈了几十年,有两种观点或做法最常见:一是主张京剧姓京、晋剧姓晋、粤剧姓粤……强调整旧如旧,偏于守成;一是请缺少戏曲实践经验的话剧导演编排戏曲剧目,大量挪用话剧写实主义的舞台技法。在我看来,传统戏曲艺术的现代转身,恐怕需要双重继承与双重扬弃:继承民族戏曲的时空原则与美学传统,扬弃封建意识等精神糟粕;吸纳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某些观念与技法,扬弃其对一切理性、逻辑极端化解构的虚无主义态度。

▍《一蓑烟雨》剧照
戏曲艺术的创新既需要有理论自觉,又必须要有舞台实践的经验和能力。苏东坡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说:“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当,不学之过也”。学而尚有高低深浅之分,凭空说嘴是上不了台面的。《一蓑烟雨》的编导、演员、舞美、作曲,都是热爱舞台艺术的实干家,不趋附时人所好,不迎合世俗趣味,持守自己的艺术信念,“欣然起行”,虽然《一蓑烟雨》尚有一些错漏扞格之处和巨大的拓展空间,但即便是当前已取得的成就,也决非是那些分切国家文艺基金这块大蛋糕的承应戏所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