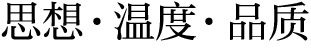2020-03-10 20:57
1920年,罗素访问中国,在杭州时,看到西湖风光,罗素大加赞赏,“那是一种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过意大利”。当时天气很热,罗素他们坐轿子翻山,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轿夫歇息十分钟。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我记得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
作为一个外国游客,罗素赞扬中国轿夫的乐观友善,这不能说有什么错,至少跟那些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的“洋大人”有着本质区别。但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鲁迅,却很不以为然,他在《灯下漫笔》中讽刺道:“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就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鲁迅是从来不信“神”的,即使对被奉为神的罗素也如此。
长沙,引发一场论战
杭州、南京之后,罗素又溯江而上,长江上的航行也让他心旷神怡,“与在伏尔加河上旅行的压抑、恐怖形成鲜明对比”。
在湖南长沙,杜威和罗素,当时世界思想界的两大巨擘,第一次碰面了,同来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张东荪、吴稚晖等中国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蔡元培即将往欧美作为期10个月的文化考察,在赴欧前,他特地赶到长沙,陪同罗素讲学,并当面邀请其担任北大客座教授。

▍罗素和朵拉与赵元任(左三)等友人在天台聚会
这次中外名人学术讲演大会,可谓风云际会,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一位书记员。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署名“杨端六讲,毛泽东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参加和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他不仅前往听讲演,还应邀担任讲演会的特约记录员。
美国人杜威在长沙讲的是教育哲学,学生自治;而英国人罗素,讲的正是毛泽东最关心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因此毛泽东给罗素当速记员自然是顺理成章。
讲台上的罗素一派英国绅士风度,神采奕奕,口若悬河,赵元任更是出彩,能用湖南方言进行翻译,并且给英式幽默中的双关语也找到中文的对应词,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显然,罗素比杜威更有人格魅力,但奇怪的是,他在观众中得到的认可却远比不上杜威。
社会主义有很多流派,罗素信奉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它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奉行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
正因如此,罗素一会儿劝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会儿又对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模式提出严厉批评。由于不能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一个一锤定音的解决方案,观众先是疑惑不解,“最后是讥评四起”。
思想激荡之后,毛泽东在11月中下旬写出了自己的想法,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这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当时三十岁出头的张东荪,是上海《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自称对罗素“佩服到一百二十分”。他回上海后,在11月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的文章,把罗素说成是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
这篇文章本就有断章取义或假传圣旨之嫌,又与布尔什维克思潮迎头相撞,引得陈独秀率先发难。他在公开信中对罗素表示不满: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也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据说,罗素曾给陈独秀回过信,但是中途遗失了。不过,即便收到了,恐怕也难以让陈独秀满意。此后,许多左翼人士都以为罗素是站在张东荪一边的。
12月,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左派们火力全开,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借着讨伐张东荪,重炮猛轰了一通基尔特社会主义。
以“南陈北李”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中国若要发展社会主义,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这种改良的方法,不仅“理所不可”,而且“势所不能”。
关于改良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论战,跌宕起伏。罗素本人肯定没想到,他的中国之行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重要一环。
依据现有资料,人们甚至无法证实罗素看到了陈独秀的公开信。他从未回应这场论战,只在自传里写了一个笑话:
我要离开北京时,一位中国朋友赠我一块极小的手刻板面,上的字迹细微难辨,他又将这段文字用优美的书法写出送给我。我问他这段话说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等您到了家的时候去问翟理斯教授吧。”我听从他的意见这样做了,才知道那是一段“巫师卜辞”,在这段卜辞中,巫师只是劝向他求卜的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位中国朋友是拿我打趣,因为我总是拒绝对中国人当前的政治难题给他们提出建议。
很长一段时间,罗素都避免谈到“中国改造”的问题,更很少直接回答或给予明确的答案,总是以“对中国问题尚待观察和思考”为由,予以婉拒。恐怕他心里也清楚,自己说的话不过是“巫师卜辞”。
吊诡的是,罗素遭到“进步的中国人”抵制时,却差点因为在华宣传“危险思想”而被北洋政府驱逐出境。所谓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他撰写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文,上海的共产党小组曾将此文印为传单。
北大,每周讲学两次
罗素于10月31日抵达北京。讲学社给他的待遇,比原先约定的还要优厚许多,除负责所有差旅费外,支付的酬金足够租住一所宽敞的四合院。罗素与朵拉、赵元任一起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2号,他们用中式的古董家具布置房子,还雇用了专门的厨师、家童、人力车夫和裁缝女佣,生活相当舒适。
 ▍罗素和朵拉在北京的住所
▍罗素和朵拉在北京的住所
他们经常把星期一作为休假日,并时常到天坛去做一日游。“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筑了。我们会无言默坐,沐浴着冬日的阳光,沉湎在和平静谧之中,然后离开那儿回来准备以镇定和平静的心情面对我们自己那个混乱的欧洲大陆的疯狂和苦痛。”
11月19日,讲学社在北京美术学校礼堂为他举行欢迎会。也许是对社会主义论战有所感触,梁启超致欢迎辞,并借此亮出讲学社不分地域门户的宗旨。他说:“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至于讲学社,好像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买哪样就买哪样。”
不过,梁启超的胸怀并不是谁都有的。据赵元任晚年回忆,胡适告诫他要小心,不要上了进步党的当,并试图阻止他应聘罗素的翻译,因为胡适认为,梁启超等人想借机“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
对于胡适的抵触态度,梁有所耳闻,并主动与他沟通过。1920年8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罗素事。”不过,胡适对罗素始终心怀芥蒂,访华九个月中,他俩连一面之缘都没有,甚至最后罗素的告别演讲,也因“为雨后泥泞所阻”未能如愿。胡适自己笑称“无缘”,其实是“无心”。
或许是为了表明讲学社并无“挟洋自重”之意,梁启超等“研究系”人士与罗素没什么深交。在北大,罗素每周讲学两次,到1921年3月为止,除了临时追加的一些单篇讲演外,陆续还进行了5个系列的讲座:“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均与研究系的主张无关。
北大师生还发起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每周参加他们的讨论会,自然也想把“绝活儿”数理逻辑,传授给这些资深的中国弟子。但他只讲过一次,学生都说听不懂,还抱怨这不是哲学。连罗素都不得不承认,这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除一人是满清皇族外,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不想听技术哲学,只需要社会改造的建议。
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
深入到学术领域的交流后,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生,罗素自己也开始抱怨:“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
不难想象,罗素在华十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却知音难遇。他也直言不讳地写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些习气的看法,比如:“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罗素、杜威、赵元任在中央公园合影
▍罗素、杜威、赵元任在中央公园合影
1921年春,在保定育德中学的一次演讲中,礼堂没有生火,而绅士的罗素坚持要脱掉外套演说,结果引发肺炎。连日高烧,最后竟至病危,不得已请杜威为他拟好了遗嘱的草稿,还作为见证人在委托书上签了字。
日本报纸未经核实就发布了罗素的死讯,这个消息从日本传到美国,又从美国传到英国,和罗素离婚的消息登在同一天出版的英国报纸上,也让罗素读到了各种对于自己的讣告。作为报复,罗素日后回敬日本记者一个字条,“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自传中,罗素还打趣说,中国人要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这并没有成为事实,我感到有点遗憾,因为那样我本会变成一个神,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那倒颇为风雅。”
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肺炎这一关,让他成了和杜威一样长寿的哲学家。不过,他早已无心逗留,只想提前离开中国。在给英国情人的信中,他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
另外,朵拉此刻已经怀孕,这是罗素的第一个孩子,他已经四十九岁了,一直期盼着自己能有个后代,此时他只想回英国迎娶朵拉,给孩子一个名分。
7月,刚能拄着拐杖行走,他就迫不及待地买好了船票,准备与杜威同日离京。作为送给中国的礼物,他在欢送会上,作了《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演讲。这次,他再无保留,一口气为中国提出了十几条建议。
 ▍罗素和朵拉临别前与《罗素专刊》同仁合影。后排:从左到右,瞿世英、赵元任、王庚、孙伏园,前排:从左到右,蒋百里、朵拉、罗素。
▍罗素和朵拉临别前与《罗素专刊》同仁合影。后排:从左到右,瞿世英、赵元任、王庚、孙伏园,前排:从左到右,蒋百里、朵拉、罗素。
最让中国人吃惊的是,他不再含糊其辞,而是就中国的现实问题、走什么道路开出一剂药方:国家社会主义。他说:“在目前产业幼稚、教育不普及的中国,不能模仿西方的模式采用民主的体制,而必须经过一个专制的过渡期。若避免资本主义而发展实业,需仿效俄国的方法,第一步惟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为最切当。”
“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也是罗素最终指给中国人的方向。对此,保守派和改良派自然是强烈不满。
张东荪对罗素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罗素离华半个月后,他在《后言》中抱怨这段离别赠言“有许多地方和他向来的主张相矛盾”,“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
就连胡适都发现了:罗素虽然是梁启超请来的助战者,却也是一位与他们的主张不那么合拍的“助战者”。他作了一首题为《一个哲学家》的诗来奚落他:“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的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傅铜辩护道:“罗素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对欧美各国最合乎理,与他劝中国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无冲突;因为欧美与中国情形不同,罗素提出的方案也不同。”
为什么临别赠言与刚来时的论调不一样了呢?中英文化交流会常任理事李丹阳认为,与很多易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不同,具有怀疑特质的罗素,不仅怀疑权威,也怀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断以现实观照理论,修正对社会的认识。他这番话是在华经过近一年的观察和深思熟虑后才讲的。
巧合的是,就在罗素离开中国的当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
7月10日,蹒跚而行的罗素离开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以双方面的失望告终: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寻到解药;中国人更失望,因为罗素太难被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了。
相对于中国人要么崇拜,要么质疑的二分法,罗素则公正得多,他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不理解和诋毁,而失掉同情心和理解力,并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的热忱。
1922年,罗素对自己的中国之行加以总结,写就了《中国问题》一书 ,这也使他成了西方最走红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尤为难得的是,在中国最孱弱的时候,书中就预言中国必将崛起,并且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他期待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在把强敌扫地出门时,也能留住中华民族特有的“温文尔雅,恭敬有礼之风,率真平和之气”。
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无原则的溢美之词。他告诫中国人不可采取的两个极端态度——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即使今天,在对待外来文化时也依然适用。而他所批判的中国人的“贪婪、怯懦、冷漠”,不也是相当深刻吗?
“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正是出于这种深切的理解,他呼吁英国当局归还庚子赔款,并将香港和威海卫归还中国;当中国发生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战争时,他激越地为大洋彼岸辩护;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杜威等发表公开信,严正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假如早一点善待新中国,世界局势当已好转。”为此,他在朝鲜战争时斥责过美国总司令麦克阿瑟,也曾出面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这是当时国际最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之一。
一份2008年解密的档案显示,罗素曾致电周恩来和他的剑桥校友兼老朋友尼赫鲁,敦促双方尽速停火撤军。对于罗素的来信,总理还回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中印边界的历史形成问题。
罗素不仅把中国的立场传达了出去,还派助理到边界调停。当时为中国说话的人确实不多,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决定请罗素访华,并请何兆武等学者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不过,罗素年事已高,终究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来。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他既激进又保守,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恐怕,才是罗素,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涵。(责编:黄加佳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