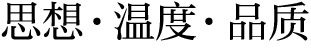2021-06-18 09:19

近年来在评价大学时,论者往往会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并且大多是用此话来批评当今的大学纷纷建大楼。
不过梅贻琦此话的本意,只是强调大师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就轻重缓急而言,大师应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大楼一时没有还可以克服,而要是没有大师,就不成其大学了。但他并没有将大师与大楼完全对立起来,更不意味着大学有了大楼就不能出大师,或者将大楼拆了大师就应运而生。
实际上,在梅贻琦当校长期间清华大学就有了很好的大楼。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清华图书馆查古籍,第一次走进老图书馆;以后又有机会在小礼堂作讲座,在老建筑中录制节目;不禁惊叹清华的“大楼”竟有那么高雅,那么宏敞,而那时的清华才二千多学生。这更证明,将大师与大楼对立起来,绝非梅贻琦的本意,更不是中国大学的传统。相反,只要稍有条件,中国的大学就会兴建或改善“大楼”——校园、校舍和各种设施,毕竟这是学校安身立命的场所,也是师生须臾不可或缺的条件。
但此“大楼”不是彼“大楼”,不是贵族的府邸、巨贾的豪宅、名流的雅舍,更不是帝王的宫殿、宗教的神坛、官僚的衙署,也有别于喧腾的市廛、闭塞的村落、摩天的高楼,而是一座与“大学”这个名字相称的真正的“大楼”,有自己的功能、自己的特色,更有自己的风骨。

这些“大楼”都称得上大,无不气度恢宏。前些年去武汉大学,看到复建的校门,突出在校园之外,以为这就是原来校园的范围。后来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建校就规划的校园比这范围更大。我一直抱怨我们复旦大学校园的拥挤局促,有一次在讨论学校规划时得知,国权路、政肃路一带原来都是学校已购置的土地,到了“大跃进”时才用来支援生产队养猪、搞生产,让居民建住房。不少老大学都是在上世纪前期规划建设的,有些大学还是私立的,学校师生数量不多,初创时往往少得可怜,那时的中国很穷,政府穷,民众更穷,却舍得为大学花钱,花大钱,还留下那么大的发展余地!
这些“大楼”充分体现尊师重教,以人为本的宗旨。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甚至省立大学,在学校的建筑、设施和功能方面大多以一流为目标,直追欧美苏,以充分满足师生教学、科研、实验、实习、体育、娱乐、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如燕京大学画栋雕梁、曲径小院的仿古建筑内,电灯、电话、暖气、热水、浴缸、抽水马桶等当时最先进的设施一应齐全。清华、燕京等校当时的教师宿舍至今令教授追忆或艳羡。复旦在1956年建了一批教师宿舍,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时年45岁,迁入了一套四大一小,带厨房、浴室、走廊、阳台的教授房。为陈望道校长和两位副校长建的是独用小楼,校方还宣布今后将为教授们建与副校长住所类似的小楼。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有宽敞的住宅,助手可以来家工作,也可在家为青年教师讲课。为了让双目几近失明的他能在甬道散步,还专门漆成白色。
这些“大楼”并不追求豪华辉煌,却为体现人文、传承文化、适应环境而刻意求工,中外建筑师由此创造了很多不朽的建筑。燕京大学的校舍校园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的,一座座殿堂院落在湖光山色、古树名木中错落有致,宛然当初的皇家园林。连一座现代水塔,也以宝塔造型成为画龙点睛的重要景观。即使一些完全西式的校舍校园,也不显得突兀张扬,在异国情调中融入了中国元素。
中国近代和当代的大师,相当一部分就曾经在这些“大楼”中工作和生活,作出了他们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从这些大楼中走出的莘莘学子,已经成为国家栋梁、社会中坚、专家学者、教授、院士、学术大师、诺贝尔奖得主。这些“大楼”是中国大学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的构成部分,是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
岁月流逝,人事沧桑,这些“大楼”或已是风烛残年,或已受到人为破坏,大多已难完好。有的甚至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依靠老照片和回忆录来想像它们当年的风采。所以当我读到顾嘉福与陈志坚先生主编的《傲然风骨——大学里的老建筑》一书后,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些文字,作为对两位有心人的感谢,也希望将本书介绍给更多读者。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于2014年1月6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