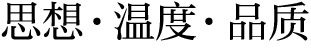2020-08-05 22:18
今年,历时13年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进入尾声,全国2760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270余万部古籍拥有了“身份证”。而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收录了781家单位的藏书约6万多种,13万部。
仅从数字的对比看,就足以令人震撼。此间,众多“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现身”,大量“命悬一线”的古籍“起死回生”。
普查开展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们都有隐隐的担忧,这项工作涉及单位众多,数量不明,最终到底能不能抵达目的地?
然而,古籍普查工作者眼中,“书卷多情似故人”,他们时刻把“不教书林有遗珠”的责任放在心中。
故纸堆里破“谜案”
埋头故纸堆,在许多人眼里未免有些沉闷乏味。而在古籍保护工作者的眼中,它却是意趣盎然的。
北京地区古籍收藏历史悠久,收藏数量庞大,很多古籍收藏单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清代。不过,许多古籍都收藏在基层单位,缺乏专业人员进行登记、鉴定。为此,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了“流动办公室”,派出普查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市属单位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开始了古籍“发现之旅”。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古籍普查
当古籍普查小组的工作人员来到这些藏书单位,对古籍像“上户口”一样,一本一本进行登记。题名、卷数、作者、版本、装帧、版式、册数、存卷、破损程度等一项不落地记录在案,并进行拍照留影。
60后的杨之峰从北京大学毕业,到首都图书馆参加工作,就与古籍打交道,迄今已经有三十年了。在他眼里,古籍普查工作就像“破案”一样有趣,古老的文献就是一个个沉默地等着你猜出身份的“老友”。
片纸只字,打着神秘的“哑谜”;断语残言,又透露出真相的蛛丝马迹。
“比如这本书,上面没有作者名号和出版者信息,当初在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费了一番功夫。”杨之峰指着一本题为《旧学四种》的线装古籍介绍道。
在这本书中,作者留下的身份信息是他的一个“号”——“东海褰冥氏”。那么,这位“东海褰冥氏”究竟是谁呢?工作人员拿出了普查工作中最常用到的工具书之一——《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进行查询。按照书中的记录,原来“东海褰冥氏”是清末谭嗣同的别号。
为了印证这个结论,他又翻开《中国现代人物大辞典》,找出谭嗣同的词条。果然,“东海褰冥氏”正是谭嗣同的“别署”,词条中还提到了谭嗣同的几篇文章名称——“寥天一阁文”“石菊影庐笔识”“莽苍苍斋石”,恰好是《旧学四种》这本书的几个小标题。
寻踪觅影,抽丝剥茧。一桩“谜案”就这样被古籍“侦探”们通过推理判断揭开了真相。“北京古籍普查过程中,几十万册古籍的信息,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录入的。”
而这个“普查小分队”在至今长达13年的探寻过程中,还曾有过不少出人意料的发现。比如,他们在为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进行古籍鉴定的过程中,就曾发现了乾隆时期的内府藏书——《班马字类》。

《班马字类》
《班马字类》在清代的用途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字典。为什么说它珍贵呢?正是因为在它上面盖着几个乾隆皇帝的玉玺印章——“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八徵耄念之宝”。
“这些都是乾隆皇帝的私人收藏印章,只有收藏到了极为珍贵的书画作品,他才会盖上这几个‘戳儿’,显示自己已经收藏过了。”据介绍,凡是同时动用了这几个印章的古籍,全部被收藏在了乾隆自己的书库“天禄琳琅”里面。
熟悉角落有“贵客”
北京市属古籍收藏单位有40余家,古籍80多万册。藏书单位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公共图书馆有16家,中学图书馆10家,高校图书馆5家。从行业分布看,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30万余册,高校和中学图书馆馆藏10万余册,文物系统图书馆收藏9万余册。
有些古籍深藏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书库,有些古籍却躲在我们身边不起眼的角落,静静蒙尘。
“令人意外的是,在北京的中学里,也‘藏’着不少珍贵的古籍文献。”“普查小分队”成员邸晓平说,这些在普查过程中发现的古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静守一隅”,却始终被“熟视无睹”。
一批与众不同的古朴书籍就藏身在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的图书馆里,学校的老师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它们的与众不同。但,它们都是“谁”?它们怎么来的?该怎么对待它们?老师们没有把握。
学校向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发出求助,普查小组的工作人员来到二十四中,为这批古籍查“身份”、上“户口”。邸晓平记得,第一次来到二十四中图书馆是2015年9月,那时这些古籍刚被二十四中图书馆的老师挑选出来。
由于年深日久,书籍的表面落满厚厚的尘土。于是,出于对古籍的保护,在登记之前,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先对它们进行了专业的除尘。
拂去尘埃,露出真容。
除尘的过程在邸晓平眼里,是有仪式感的。“这个拂去尘埃的过程,仿佛昭示着普查工作对于古籍保护的意义所在。每完成一次,大家对工作的认同和热爱就又在心里默默深化一次。”
除尘之后,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帮助学校对古籍进行了整理、编目、制作书签。最终,二十四中终于弄清了自己的古籍“家底儿”——共藏有线装书641种4000余册,“其中古籍362种2885册,抄本、刻本皆有,经史子集四部俱全。”
这些古籍收藏是怎么来的呢?那还要从二十四中的“前世今生”讲起。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创建于1923年6月1日,前身为北京私立大同中学,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蒋梦麟、谭熙鸿、丁燮林、颜任光几位北京大学教授共同创办的。它的校址位于东城区外交部街31号,原为明代将领李成梁的府第,后为清睿亲王新府。
普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们查阅资料得知,二十四中的古籍藏书包括睿亲王新府原藏一定数量的古籍,北京私立大同中学的几位创始人带来的一些古籍,以及后来校方采购增加的一些古籍。
“不过,二十四中在历史上曾经历几校分分合合,书籍搬动转移,年深日久,也有部分古籍书叶破损比较严重。”因此,古籍保护中心派出修复专家,对部分破损古籍进行了修复。
了解,正是珍视的第一步。
北京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时刻关注着这些曾掩埋在历史尘埃中,又被他们亲手寻回的古籍的境遇。邸晓平说,目前,二十四中的古籍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学校对古籍保护十分重视,正在申请筹划建立编目系统和恒温恒湿的专业书库。”
雪域高原探“秘史”
2010年7月,西藏古籍保护专项活动启动后的第二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来到西藏图书馆。此后的三年中,她与西藏古籍普查工作一同前行。
在那里,她与沉眠于雪域高原的《蒙古秘史》不期而遇,一段奇缘让身为蒙古族人的她,每每想起总会心绪难平。

《蒙古秘史》
2011年3月,西藏阿里地区全面启动了古籍普查工作。在闻名雪域的古刹——托林寺内,普查工作者曾意外发现了不知为何文的古籍散叶,并求问于萨仁高娃。萨仁高娃通过辨认图片内容,认为是成书于距今900多年前的,记述蒙古民族500多年形成、发展、壮大历史的著作——《蒙古秘史》。
2012年10月,萨仁高娃和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奔赴阿里,在地区文化局古籍办工作人员及札达县文广局局长带领下,对托林寺所藏古籍的普查工作进行查漏补缺。那是一段她难以忘怀的经历。
藏区的古籍普查之路艰辛异常。车陷在泥泞的山路上,打滑几近坠崖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山路不通的地方,普查队员只能骑马或徒步,艰难跋涉。夜幕降临,普查队员们燃起篝火,在羊圈中露营过夜。

西藏普查人员骑马渡河赶向普查点
艰难的路,映衬着执着的心。
无心休整,一往无前。数天跋涉,一行人直奔象泉河畔的托林寺。10月17日,这个日子萨仁高娃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在那天午后,她亲眼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蒙古文散叶。
得知古籍保护工作者们的来意后,住持从佛殿深处取出仍用旧报纸包裹的散叶交给萨仁高娃。手捧散叶的瞬间,她双手颤抖,心跳加速。来自民族和血脉的亲切感涌上心头,令她情不自禁地低头膜拜。随后,她缓缓打开旧报纸,将散叶放在临时搭起的小桌子上,默默注视,泪水在眼圈里打转。
略微发黄的梵夹装纸张上书写的古朴蒙古文赫然眼前,诉说着千年往事。
萨仁高娃在征得同意后,对托林寺发现的散叶进行拍照,并潜心研究。托林寺仅存的11叶《蒙古秘史》,每叶正面左侧用蒙古文写有页码,存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叶(其中两叶仅存照片资料)。内容涉及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抢去,铁木真经王汗与扎木合的帮助,抢回孛儿帖,后与扎木合决裂的一段内容。
尽管仅存11叶,却是近年所发现的最为珍贵的蒙古文史料。
萨仁高娃说,这些散叶作为《蒙古秘史》民间流传的异本,势必为资料欠缺而难于推进的百年“秘史学”研究输入新鲜血液,带来一次巨大的震撼。

萨仁高娃与《蒙古秘史》
一部蒙古文历史文献,能够传入西藏,并在当地得到抄写,本就是一段传奇。而在古籍普查中,又被一位蒙古族学者发现、研究,揭示历史谜底,因缘巧合更令人称奇。
走向更深的“书海”
按计划,全国的古籍普查工作将在今年基本完成。
截至去年底,全国古籍普查完成总量达270余万部1.8万函,已占预计总量的90%以上。全国已有2760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古籍修复总量超过360万叶。而古籍普查的成果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给公众,“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资源总量超过3.3万部1500余万叶,国家图书馆超过2/3的善本古籍已实现在线阅览。
不在沧海留遗珠。尽全力不让一部古籍被遗忘在尘封的角落,这是每一位古籍普查工作者的“初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管理组组长洪琰说,许多基层藏书单位仅零零散散藏有很少量的古籍文献,但它们也没有被普查的目光遗漏。比如,在一个县级小馆——重庆市垫江县图书馆就仅发现了一种古籍:《康熙字典》。而它也如其他所有珍贵的古籍善本一样,被列入了普查登记的目录。
“家底儿”终于摸清了,普查工作者的探索会就此告一段落吗?当然不会。洪琰说,事实上,在这十余年的历程中,作为全国范围内古籍普查登记的组织和协调者,她曾有过许多彷徨和挣扎的时刻。
最开始,古籍普查的登记表被称为“十六表”,里面的注录项目都是经过专家们深思熟虑、数度研讨的结果,全面细致得超乎常人想象。而如今,最终呈现给读者、公众的登记项目中,必填的只剩下六项。
壮士断腕,以全其质。
在十余年的艰辛实践中,遇到过许多进退维谷的艰难时刻。基层单位古籍保存的现状,编目人员业务水平的局限,种种因素牵绊着古籍普查工作前行的脚步。而为了将古籍普查更好地推进下去,唯有披荆斩棘。
“作为古籍保护工作者,这样的割舍,一度让我难以接受。”然而,图书馆绝不仅仅是储存知识的宝库,更是传递知识的载体。有舍才有得,只有将工作推进下去,将古籍普查数据尽早揭示出来,才能让公众尽早享受到古籍普查的成果。想到这里,洪琰感到欣慰的同时,又感叹上下求索的道路依然漫长。
正因为有这样的割舍,才说明,对于古籍普查工作者来说,值得发掘和拓展的项目还有很多,值得深挖和书写的内容还有很多。
“古籍普查工作并不会就此‘告一段落’,它只会向‘书海’更深处走去。”洪琰笃定地说。